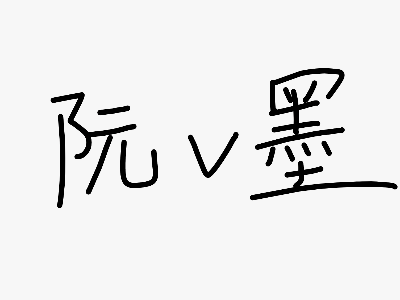导图社区 《寒梅映雪,墨染相思》19.
- 96
- 2
- 6
- 举报
《寒梅映雪,墨染相思》19.
这篇是皖的原创小说《寒梅映雪,墨染相思》第19章,感兴趣的宝宝点点赞,谢谢。禁仿,抄袭和搬运。重发。
编辑于2025-10-25 10:06:44- 小说
- 更文
- 阮清颜-墨宸渊
- 相似推荐
- 大纲
《寒梅映雪,墨染相思》19
第十九章江南春暖,医馆初开
江南的春天来得格外早。 三月的雨丝裹着新茶的香气, 斜斜落进青石板缝里, 将巷口那株老杏树润得愈发娇艳。。
阮清颜站在医馆门前, 望着门楣上"悬壶居"三个鎏金大字, 指尖轻轻拂过墨宸渊亲手题的字--他的字向来清瘦刚劲,此刻却多了几分圆润, 像极了江南的烟雨。
"姑娘,该挂招牌了。" 学徒阿朱捧着红绸站在梯子上,声音里带着雀跃, "这是王爷特意让人从京城送来的樟木牌匾,说是要沾沾京城的福气。"
阮清颜笑着应了, 转身时却撞进一堵温热的胸膛。 墨宸渊的玄色锦袍还带着晨露的湿润, 发间插着支青玉簪子, 是他昨日在山塘街替她挑的"配你素色裙衫, 好看。”
“发什么呆?"他的声音低哑, 带着刚睡醒的慵懒,"昨日替你熬药到三更, 今日倒比我还精神。"
阮清颜偏头看他,见他眼尾还带着淡淡的青影, 忍不住伸手戳了戳他的脸颊: “谁让你总熬夜看账本?医馆的账册你看得比兵书还认真。"
墨宸渊握住她的手,放在唇边轻吻: "这医馆是你的心血,自然要仔细。”
他指腹摩挲着她腕间的银镯--那是他用当年父亲留下的碎银打的, "昨日张婶说,隔壁王阿婆的风湿又犯了, 你待会儿给她扎针时,记得用新制的艾绒。"
“知道了,墨管家。"阮清颜故意板起脸, 眼角却弯成月牙。
医馆刚开张,来看病的大多是街坊邻居。有个卖豆腐的阿婆腿肿, 阮清颜用外敷的药膏给她消了肿;
有个读书郎中了风邪,墨宸渊亲自为他针灸, 扎完针还逗他背《论语》 --那孩子背到"君子不器”时卡了壳,急得抓耳挠腮,倒把众人逗得直笑。
日头偏西时,医馆里忽然安静下来。 阮清颜正低头整理药柜,忽闻见一阵沉水香, 抬眼便见墨宸渊倚在门框上,手里端着碗刚熬好的枇杷膏。
"今日的药钱,够买十筐枇杷了。"他将碗递给她, 眉梢微挑,"阿朱说,你给那小乞丐扎针时, 把金针都送了。"
阮清颜接过碗,舀了一勺含在嘴里, 清甜的枇杷味漫开:“那孩子咳得厉害, 金针扎几次就能好,比吃药管用。"
“你呀。"墨宸渊摇头轻笑, 伸手替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, "总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。"
话音未落,门外忽然传来喧哗。 几个穿玄色劲装的人踢开木门冲进来, 为首的脸上有条刀疤,腰间悬着墨家特有的玄铁令牌。
“阮清颜!"刀疤男冷笑, "别以为躲到江南就安全了。墨宗余孽, 也配开医馆?”
阮清颜的手微微一颤,枇杷膏险些洒出。 墨宸渊立刻将她护在身后,目光冷冽如刀: "墨三,你倒是阴魂不散。"
"王爷别来无恙。"刀疤男上下打量着墨宸渊, "听说您为了个女人,连皇兄的恩宠都不要了? 如今落得个闲散王爷的下场,倒不如……"
“住口!"墨宸渊打断他,声音里淬着冰, "当年阮家的事,你参与了几分?"
刀疤男脸色骤变,后退半步:“我…… 我只是奉命行事!”
“奉谁的命?"阮清颜上前一步,声音清亮, “是当今圣上?还是墨宗的老祖宗?"
刀疤男被她问得哑口无言, 突然从袖中抖出把淬毒的短刃, 直取阮清颜咽喉!
“小心!”墨宸渊旋身将她推开, 短刃擦着他耳畔钉入门框,木屑飞溅。
阿朱尖叫着躲到柜台后, 几个看病的百姓也慌忙往外跑。墨宸渊抽出腰间软剑,剑花如电,瞬间便将刀疤男的短刃挑飞。
刀疤男还想反抗, 却被他一脚踹中胸口,撞在墙上昏死过去。
“王爷!”阮清颜扶住他的胳膊, 见他肩头渗出鲜血-一方才那一下, 短刃虽未伤到他,力道却震得他旧伤复发。
墨宸渊却笑了, 用没受伤的手替她擦掉脸上的药渍:“你慌什么? 我还没老到连个毛贼都打不过。"“谁慌了!"阮清颜别过脸,耳尖泛红, "我是气你总不爱惜自己。"
这时,巷口传来铜锣声。 几个手持水火棍的衙役冲进来, 为首的捕头见到墨宸渊,连忙躬身:“属下苏州府衙张捕头,奉知府大人之命, 特来请墨王爷回府--说是……宫里来了圣旨。”
墨宸渊挑眉:“圣旨?”
张捕头赔笑道:“小人也不清楚,只听说是关于……双忠碑的事。"
TvT坏事了。我还没装扮,就不小心发出去了。不要在意前面那个费稿。TvT我删掉啦,我看不顺眼TvT。重发一遍,流量up up up。@沈和@Y,快更新。TvT 沈退的原因我知道,但我不能说。知道是因为学业原因退的就好TvT
《寒梅映雪,墨染相思》19
第十九章江南春暖,医馆初开
江南的春天来得格外早。 三月的雨丝裹着新茶的香气, 斜斜落进青石板缝里, 将巷口那株老杏树润得愈发娇艳。。
阮清颜站在医馆门前, 望着门楣上"悬壶居"三个鎏金大字, 指尖轻轻拂过墨宸渊亲手题的字--他的字向来清瘦刚劲,此刻却多了几分圆润, 像极了江南的烟雨。
"姑娘,该挂招牌了。" 学徒阿朱捧着红绸站在梯子上,声音里带着雀跃, "这是王爷特意让人从京城送来的樟木牌匾,说是要沾沾京城的福气。"
阮清颜笑着应了, 转身时却撞进一堵温热的胸膛。 墨宸渊的玄色锦袍还带着晨露的湿润, 发间插着支青玉簪子, 是他昨日在山塘街替她挑的"配你素色裙衫, 好看。”
“发什么呆?"他的声音低哑, 带着刚睡醒的慵懒,"昨日替你熬药到三更, 今日倒比我还精神。"
阮清颜偏头看他,见他眼尾还带着淡淡的青影, 忍不住伸手戳了戳他的脸颊: “谁让你总熬夜看账本?医馆的账册你看得比兵书还认真。"
墨宸渊握住她的手,放在唇边轻吻: "这医馆是你的心血,自然要仔细。”
他指腹摩挲着她腕间的银镯--那是他用当年父亲留下的碎银打的, "昨日张婶说,隔壁王阿婆的风湿又犯了, 你待会儿给她扎针时,记得用新制的艾绒。"
“知道了,墨管家。"阮清颜故意板起脸, 眼角却弯成月牙。
医馆刚开张,来看病的大多是街坊邻居。有个卖豆腐的阿婆腿肿, 阮清颜用外敷的药膏给她消了肿;
有个读书郎中了风邪,墨宸渊亲自为他针灸, 扎完针还逗他背《论语》 --那孩子背到"君子不器”时卡了壳,急得抓耳挠腮,倒把众人逗得直笑。
日头偏西时,医馆里忽然安静下来。 阮清颜正低头整理药柜,忽闻见一阵沉水香, 抬眼便见墨宸渊倚在门框上,手里端着碗刚熬好的枇杷膏。
"今日的药钱,够买十筐枇杷了。"他将碗递给她, 眉梢微挑,"阿朱说,你给那小乞丐扎针时, 把金针都送了。"
阮清颜接过碗,舀了一勺含在嘴里, 清甜的枇杷味漫开:“那孩子咳得厉害, 金针扎几次就能好,比吃药管用。"
“你呀。"墨宸渊摇头轻笑, 伸手替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, "总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。"
话音未落,门外忽然传来喧哗。 几个穿玄色劲装的人踢开木门冲进来, 为首的脸上有条刀疤,腰间悬着墨家特有的玄铁令牌。
“阮清颜!"刀疤男冷笑, "别以为躲到江南就安全了。墨宗余孽, 也配开医馆?”
阮清颜的手微微一颤,枇杷膏险些洒出。 墨宸渊立刻将她护在身后,目光冷冽如刀: "墨三,你倒是阴魂不散。"
"王爷别来无恙。"刀疤男上下打量着墨宸渊, "听说您为了个女人,连皇兄的恩宠都不要了? 如今落得个闲散王爷的下场,倒不如……"
“住口!"墨宸渊打断他,声音里淬着冰, "当年阮家的事,你参与了几分?"
刀疤男脸色骤变,后退半步:“我…… 我只是奉命行事!”
“奉谁的命?"阮清颜上前一步,声音清亮, “是当今圣上?还是墨宗的老祖宗?"
刀疤男被她问得哑口无言, 突然从袖中抖出把淬毒的短刃, 直取阮清颜咽喉!
“小心!”墨宸渊旋身将她推开, 短刃擦着他耳畔钉入门框,木屑飞溅。
阿朱尖叫着躲到柜台后, 几个看病的百姓也慌忙往外跑。墨宸渊抽出腰间软剑,剑花如电,瞬间便将刀疤男的短刃挑飞。
刀疤男还想反抗, 却被他一脚踹中胸口,撞在墙上昏死过去。
“王爷!”阮清颜扶住他的胳膊, 见他肩头渗出鲜血-一方才那一下, 短刃虽未伤到他,力道却震得他旧伤复发。
墨宸渊却笑了, 用没受伤的手替她擦掉脸上的药渍:“你慌什么? 我还没老到连个毛贼都打不过。"“谁慌了!"阮清颜别过脸,耳尖泛红, "我是气你总不爱惜自己。"
这时,巷口传来铜锣声。 几个手持水火棍的衙役冲进来, 为首的捕头见到墨宸渊,连忙躬身:“属下苏州府衙张捕头,奉知府大人之命, 特来请墨王爷回府--说是……宫里来了圣旨。”
墨宸渊挑眉:“圣旨?”
张捕头赔笑道:“小人也不清楚,只听说是关于……双忠碑的事。"
TvT坏事了。我还没装扮,就不小心发出去了。不要在意前面那个费稿。TvT我删掉啦,我看不顺眼TvT。重发一遍,流量up up up。@沈和@Y,快更新。TvT 沈退的原因我知道,但我不能说。知道是因为学业原因退的就好TvT
别删!!!